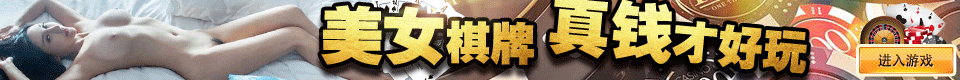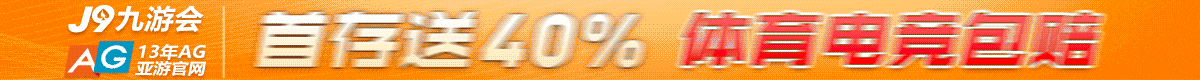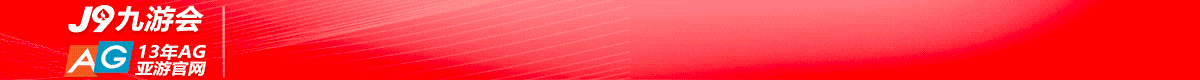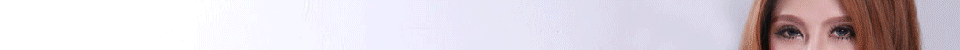茅坪奇人“华难缠”(一)
“华难缠”是他绰号,真名华敬亭,神农古镇茅坪南村坝人,生于民国,逝于解放初。凡知悉者皆称其人善言辞,多计谋,江湖怪才一个。所以乡里村院,大人小孩只管叫他华难缠,时旷日久,温文儒雅的大名及乎被人忘却了。后人只知华难缠,不知官名华敬亭,笔者收集流传民间的二三趣事辑录于后,以供读者欣赏。

迁牛记
昨天下午,在山里金大姐的助力下,我们将置于葫芦塘边的铜牛,迁回房前的草场上。牛头前的草坪绿油油,牛尾新铺的草地湿漉漉。这头牛随我们从江北城里,跨过长江到江南山中,屈指一算也有五个春秋了。我的生活渐趋宁静,牛却被我们转场了四次。

父亲的求学路
莫言写自己小时因饥饿难耐去吃黑炭,油亮光泽的炭块让他们吃得满嘴乌黑,却越嚼越香。有篇文章说——人在饥饿时,毫无灵魂可言。如若饿得灵魂都不在乎了,还会在乎一块黑乎乎的煤球吗? 我的父亲虽不至于如此困顿,但少吃没喝,依然是他们年少时黑洼洼的经历。 穷字当头,父亲十四岁才上了学,那时村里没有学校,要上学得跑到沟南,后来东城有了学校,学生娃才能就近上学。当时教他们的贺登荣老师看父亲年龄大了,就让他从二年级学起。东城学校刚开始是借用一座古庙,年久失修,学生得在自家搬桌凳。 三四年级父亲是在社堤上的学,贤良仁善的大姑姑嫁到本村,她让父亲在家里吃饭,本就缺衣少吃的年代里,大姑姑一家对父亲的疼惜与关爱,成为父亲求学路上明亮的灯火,温暖着整个记忆。 社堤学校也是占用村里的老庙,半边庙,办边教室,当时教书的薛怀让老师叫父亲作伴,抽时间给他补课。漆黑的夜晚,古庙里愈发寂静阴森,青面獠牙的神像更显狰狞。就着暗淡的煤油灯,师徒二人一个教的认真,一个学的专注。 社堤上了两年学父亲又考南村坡(一年),再转东关上了完小后考取吉县一中。 父亲上学的年代半工半读,有时候,劳动甚至挤占了一多半时间。

龚家沟,大坡上,这里是我老家,家里有老妈。又站在泉边,窃问一句:亲人们,你可曾回来?
龚家沟,现在改称桃园村,在今勉县阜川镇境内,尖山子之南,东南接新集,西至高桥沟,北通镇川。旧时顺沟而上自西向东有桃园、龚家沟、蒲家院三个自然村落,统称为龚家沟,也称老龚家沟。其实真正的龚家沟则是指马家桥、周家院、泉水湾一带,称小龚家沟(后文所提及皆指此名),周姓人家最多,张姓次之,而陆、岳等姓十余户,几姓人家互有联姻,相处融洽。